【人物專訪】馬志翔談《KANO》(上):歷史沒有對錯,人的情感才最重要
《KANO》電影甫上映,票房即已突破千萬!但這部敘述發生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棒球故事,也引起了很多朋友對於故事架構的討論。於是《Mata Taiwan》在電影上映前為大家訪問了《KANO》的賽德克族電影導演 Umin Boya(漢名:馬志翔),為眾粉絲當面詢問了許許多多的疑問……
《KANO》,球隊齊心不認輸,不放棄任何一顆球的棒球故事
建立一個三族共和的球隊,不分族群,共同朝著一個美好的目標前進,這樣的故事是不是能打動人心呢?
小編:為何會想拍《KANO》?
Umin:
2008 年左右,在創作《賽德克‧巴萊》時,魏德聖導演(以下簡稱「魏導」)就發現了霧社事件隔年,1931 年嘉農打進日本夏季甲子園的故事。魏導只是單純喜歡這個故事,但不見得適合自己去拍,所以就把劇本拿給我。可能一方面因為他對我的作品很熟悉,又是運動員,打過少棒,國中到大學都是籃球校隊,對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球類運動訓練比較熟悉,所以才覺得我可以拍《KANO》。
我們當時知道嘉農的故事後,覺得很驚訝。
電影很容易被視為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文化又跟歷史有關,而最接近現在的歷史,就是日治時期。在那個年代,有發生了很多故事,有很多壞的故事,但有沒有好的事情呢?確實有很多啊,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 其中就包括嘉農的故事!
建立一個三族共和的球隊,不分族群,共同朝著一個美好的目標前進,這樣的故事是不是能打動人心呢?
他們當時一心一意所求的不是贏球,而是不能輸,不要放棄,做任何事都不要放棄。我認為這個信念擺在現在的各行各業都行得通:機會就像一顆燙手的芋頭,擺在你手上,很燙、很燙,如果你一放手,機會就掉了,如果你堅持到底,當這個燙手山芋漸漸變暖,就會變成很可口的養分!
當時嘉農這群孩子就是不放棄任何一顆球,明明打到冠亞軍,明明知道會輸,他們還是堅持到底,最後輸了比數,卻贏得了心裡自我認同的價值。更令人感動的,是贏得敵對球迷的喝采與歡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故事。
Umin Boya,透過演戲找回自己
在我應該要驕傲的時候,卻發現部落有這麼多問題,很痛苦,就會想要解決它們……
小編:我記得您是賽德克族和撒奇萊雅族的小孩?
Umin:
我外公是撒奇萊雅族,外婆是阿美族,我爸爸那邊則是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山里部落(Mdudux)的 Toda 賽德克族(註一),從小在那邊長大,但我國小就下山。
小編:我對您的印象是來自一開始的《大醫院小醫生》、《孽子》,到《風中緋櫻》,後來演而優則導,開始自己拍戲,拍了《十歲笛娜的願望》、《我在這邊唱》、《飄搖的竹林》等一些跟原住民族有關的電影?
Umin:
我從小就一直在打球,高中也代表國家參加過比賽,但後來自己發現,自己其實沒有那麼喜歡打籃球,於是會開始想說,我到底要做什麼?
我一開始會演戲其實也只是為了賺錢。我爸很早就去世,因此我媽常希望我趕快去當兵,這樣就可以去賺錢。但是我想念書,也不是為了什麼高深的學問啦!就只是很想體驗大學生生活,然後我媽就會開玩笑說,我如果要去當大學生,我就要自己賺錢,於是我就開始打工賺錢。
一次機會下,學長介紹我一份摩特兒走秀的工作,於是我開始走秀、拍廣告,慢慢地被人注意到。我的啟蒙老師王小棣老師就是在那時候找上我,拍了第一部戲《大醫院小醫生》。一開始就只是想賺錢,雖然其實也賺得不多,但就是慢慢演出興趣。
開始演戲後,我在原民台的部落三部曲其中一部裡飾演一位很不認同自己的原住民大學生,就剛好跟我當時的心境一樣,很不認同自己的血液,但在戲裡面卻必須培著一位女孩子回到自己家鄉去尋根;在尋根的過程中,我的心裡卻開始有了化學變化。
因為我長得就是很原住民,以前念書的時候有被歧視,所以一直都不是很認同我自己。但在演過那部戲之後,我開始會想說,是不是該重新認識我自己?
於是我開始大量閱讀原住民文學、創作、歌曲,甚至於沒事就跑部落,感受一下山,感受一下海,跟老人家聊天。

那時候我差不多是大二、大三,然後在跑部落的過程中,就會開始發現很多我當時自以為是一個「文明人」所看到的問題。你說那些部落看到的現象不是問題嗎?其實也是問題。
當原、漢兩個文化碰撞在一起,小的會被大的吃掉,更可怕的是被融合,但更可怕的是原住民無法適應外來文化。這不適應,就會造就很多所謂的家庭問題、教育問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若不去解決他,就會在角落發爛、腐臭。
當時我那麼年輕,才剛找到自我認同,開始民族意識覺醒的時候,一開始有很強烈的喜悅感:「喔,原來當一個原住民這麼厲害!原來我的祖先這麼厲害!」在我應該要驕傲的時候,卻發現部落有這麼多問題,很痛苦,就會想要解決它們。
但該怎麼解決?我不會拿筆,不會唱歌,也不會搞政治,該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 我那時是個演員,那我來說故事好了!我試試看自己寫、自己拍,於是種下想要當導演的契機。我希望用戲劇描述現況,再把這些故事拍成戲劇,讓觀影者自行判斷。我提供你這些問題,把問題丟出來,讓你自行判斷。因為那時我覺得我還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也沒辦法很主觀地告訴你這樣是錯的,或這樣是對的,一來我年紀也還不到,二來我的生命經驗也還沒能讓我去解決這些問題。
於是我開始大量地創作、寫劇本,也不知道能不能拍;從大學開始,一路寫到退伍隔年。那段最憤青的時間,是我最大量創作的時候。
後來我拍的電影都是我早期自己寫的劇本,除了《飄搖的竹林》是徵求 Walis Nokan 老師(泰雅族)的許可,改編他的作品。
說到 Walis Nokan 老師,我一直覺得早期他們那一輩原住民前輩的創作比較勇敢,比較敢衝撞,很適合我當時的心情。相反地,後來年輕一輩的作品就比較浪漫。

部落是奶與蜜之地
小時候我很討厭部落,覺得部落很舊、很髒;可是長大後才發現,小時候那段日子,都是我後來得以創作的養分。
小編:在跑部落、大量創作的過程中,有什麼另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嗎?
Umin:
我記得一年春節過後,好像是花蓮的太平部落(Tavila),我知道那邊很漂亮,有山谷、有溪,就想去那邊看看那邊的人,看看那邊的老人家。
在我跑完部落,想要騎車回市區吃麵的時候,經過一個學校,當時就有兩個小朋友,應該是兄弟,坐在旁邊,於是我就想說過去跟他們聊聊好了。那個弟弟看起來很皮,我先問他:「弟弟,你在那邊幹嘛?」弟弟說:「沒有,我們在等爸爸!……」
結果弟弟還沒講完,他哥哥就「啪」一聲打下去,說「再講我揍你!」
「喔,你那麼兇喔!」我跟哥哥說。我看到哥哥用很憤怒的眼神看弟弟,於是我趕快安撫:「好啦,不要那麼生氣,趕快去上課。」
回到城鎮的時候,我在想,這兩個小鬼為何上課時間還在外面,還背著書包?他們是不是在等誰?弟弟說在等爸爸,但我想,會不會是過年的時候,爸爸沒有回來?爸爸回不回來,跟上不上課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因此沒來繳學費,孩子們不敢進去學校上課?
於是我就從這個點出發,創作一個劇本,最後就變成我第二部執導的《說好不准哭》。
創作是來自於經驗,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你不可能坐在這邊憑空想出一個劇本,就算可以,也一定也是個很難看的劇本。那段在部落跑來跑去的時光,確實是我吸取養分的時間。《聖經》裡不是有所謂奶與蜜之地?對我來說,部落就是奶與蜜之地!我這次被《KANO》炸了三年,結束之後,真的很想再去流浪半年。再一次到部落到處跑。
小時候我很討厭部落,覺得部落很舊、很髒;可是長大後才發現,小時候那段日子,都是我後來得以創作的養分。
我父親是校長,會想要我到好一點的環境讀書,所以很小就讓我到都市去,所以我跟我阿公阿嬤相處的時間太少,沒有太多機會去領受他們的教育,真的很可惜,像我的母語就講得零零落落的。
我常常跟在都市念書的晚輩說,我們這些都市原住民是灰色的。如果說現代文明是黑色,部落是白色,那我們這些灰色的人要承擔一個責任,就是擔任溝通橋樑的角色。你不可能完全變白,不可能完全變成黑,你是灰色。
灰色不可憐,有不同的觀點,看過不同的東西;就像撒古流說:「我學你們的語言,認識你們,再去保護我。」
時代在變,我除了吸收我部落的養分之外,我也有吸收到現代文明的養分,這是不能抹滅的事實;就好像說台灣原住民一直不斷地換寄養家庭,從葡萄牙人看到台灣後,經歷了西班牙、荷蘭、清廷、日本、國民黨、民進黨,又國民黨,一個接一個…… 我們現在終於找到自己是誰,但你能夠否定你的童年嗎?沒有童年,能不能有現在長大的你?
我們不能否定漢人的養分。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忘記自己是誰。

歷史沒有對錯,人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
歷史沒有好跟壞,很多時候都是在那個大環境底下,逼人家做抉擇。
小編:身為原住民導演,拍這部電影,是不是有多了什麼包袱?
Umin:
我覺得沒有包袱,純粹就是拍一個棒球電影。我以前拍的所有電影都跟原住民有關,但只有這一部,也是我第一部長片,是拍所有台灣人的棒球電影。
這不是為閩南人而拍的棒球電影,不是為客家人而拍的棒球電影,不是為原住民而拍的棒球電影,更不是為日本人而拍的棒球電影,我在拍的是日治時期當時台灣人的一部棒球電影!拍這部電影,跟我是什麼族群沒有任何關係,不是單單為原住民發聲,也不是單單為日本人發聲,是為了台灣歷史,台灣棒球史。是在闡述一個台灣美好的歷史。
當碰觸到歷史題材的時候,我的解釋是:沒有真的好人、壞人之分。歷史沒有好跟壞,很多時候都是在那個大環境底下,逼人家做抉擇。
說到日本人,我拿《賽德克‧巴萊》裡的小島源治來講好了,我問你,當你全家被殺的時候,你會不會有仇恨?
然後我們來說鐵木‧瓦歷斯,有誰可以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好人,有誰可以告訴我他是真正的壞人?他不就是站在他的位置,被他的環境所逼的時候,必須要做出他的決定?我們講到歷史,因為日本人,因為自己想要執行 Gaya(註二),鐵木‧瓦歷斯看起來是站在日本人這邊,實際上他是必須要保護自己族人不被日本人殺害。
歷史結果只有告訴我們,他為了幫日本人殺莫那‧魯道而戰死在沙場上,但歷史不會告訴我們,他的心情曲折是什麼?
回到《KANO》,為何要寫拍這部戲?我能夠想像的事,我剛剛講到,對於日治時代,我們大部分所遇到、看到的,都是不好的、無奈的、仇恨的 ── 那,有沒有好的?
以我自己為例,我從小的感受是,我的外公和媽媽都很不喜歡日本人,因為外公以前有被抓去當日本兵;但是我的爺爺,在日本人離開後,很想念日本人,很喜歡講日語,常常叫我們這些晚輩摔角給他看。是不是因為我爺爺那邊有受過日本教育,因此會很懷念日本人?
所以,拿掉政治來講,回到人身上,其實人的情感,才是我們真正想要探討的東西。
(本文下接〈【人物專訪】馬志翔談《KANO》(下):想想嘉農,台灣人應先認同自己!〉)

註 1:
賽德克族依照方言別可分為三個群:
- 德路固(Seejiq Truku)
- 德固達雅(Seediq Tgdaya)
- 都達(Sediq Toda)
Umin Boya 的父親即屬 Sediq Toda。
註 2:
Gaya/Waya 有人譯為「祖訓」,是賽德克族祖先所流傳下來的集體律法,範疇小至個人,大至整個族群群體。
相關內容推薦
- 書名:KANO 1:魔鬼訓練
- 作者: 魏德聖、陳嘉蔚/原著劇本
- 繪者:陳小雅
- 出版社:遠流
- 定價:
240元(優惠價:79折157元) - 介紹:
這是一群奮戰不懈的棒球少年,朝著夢想、豪邁前進的熱血故事!
嘉農棒球隊是一支由原住民、漢人和日本人「三族共和」組成的球隊。打棒球對他們來說,本來不過是強身健體的運動。一天,學校替他們找來了新教練近藤兵太郎,一心一意以帶他們打進甲子園為目標,並展開斯巴達式的魔鬼訓練。
在鐵血教頭近藤兵太郎的日操夜練之下,嘉農棒球隊的實力有如脫胎換骨般大躍進。但同時球隊也面臨找不到經費支援的窘境,前進甲子園的夢想不斷遭到譏諷與嘲笑,這雙重阻礙會讓他們打回原形、變成原來一盤散沙的球隊嗎?
你也有原住民或的故事要分享嗎?
也歡迎加入我們粉絲團,
每天追蹤原住民文化、權益大小事!
採訪、編輯:方克舟/圖片來源:果子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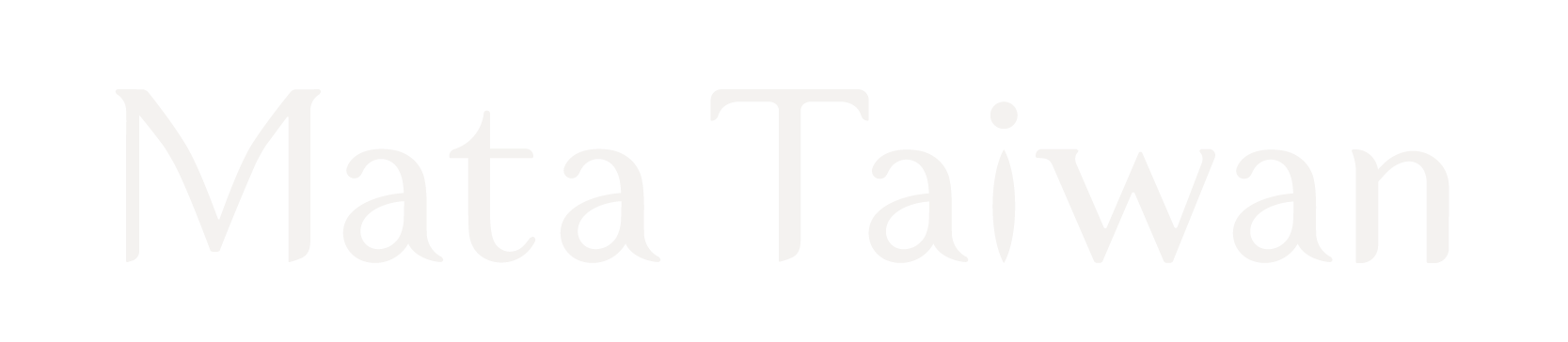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