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的人》平埔,不就是臺灣的縮影?
沒有名字的人/4 號,陳以箴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你的曾祖父跟我說的。』」── 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
一年半前的那個下午,從戶政事務所走出來,反覆確認手上的日治時代戶籍謄本。盯著外婆的爸爸種族欄上的「熟」字(編按1),狠狠記住阿祖的名字(「潘德明」),似要看穿什麼、又彷彿是責備自己怎麼未曾經心,眨一眨眼,一路哭著騎車回宿舍。
高樹庄、青埔尾、加蚋埔……,把日本官員的毛筆字跡唸出聲,赫然,自小母親帶我們在北屏東平原的各庄拜訪親戚,那些浮掠的記憶和地名,在手上這份台灣拓墾的考據史載上清晰地辨明。從沒發現北屏東平原的地名我是如此用父母親的台語熟記著,堆疊在童時記憶深處。廣陌豔陽下,屏東的縣道筆直,成排檳榔樹混揉著中央山脈尾端的氣味,與我 21 歲的生命追索交織在一起,是一種「我突然真正地認識你了」的顫慄。
練習當一個原住民,需要花多久的時間呢?是一個月、一年、還是一輩子呢?
原住民是甚麼樣子的?他們怎麼說話、怎麼想、用甚麼方式過生活呢?誰是原住民?那,我是誰?
我在高雄市長大,尋常的那種集合式大樓;我父親的父親來自澎湖七美嶼,母親則來自屏東高樹鄉。也未曾有過多少跟原住民有關的記憶,只隱約記得母親說過,她和她的堂/表姊妹們,時有被「誤認」成原住民的經驗。是一直到高三,到花蓮太巴塱部落,進雜貨店買飲料時,依南部人的習慣,下意識地對長輩說台語,發現老人家聽不懂,改說中文,還是聽不懂,才驚覺,阿嬤只會說族語啊!這個片刻非同小可,我從沒想像過,台灣有完全不能夠以中文溝通的人存在。
大學後進入了學運社團,開始頻繁地參與各種倡議、抗爭行動,從校園轉型正義到教育商品化、從南方刊物到中國營隊,當然,也包含了原住民族議題。莽莽撞撞逞少年,這一路上,為了尋找自己的著力點,竟也開啟了追索身分認同的契機。還記得第一次,參與成大原住民社團的歌舞排練,看著自己腰上層層疊疊的布、彩色的緞帶,端詳自己的樣子,感覺到族裔和身分;在每一個踏步、踮腳、領唱、答唱的過程裡,我感覺我不只是在練習歌舞,而也是在「練習」作一個原住民。沒有盡頭地。
忘了從甚麼時候開始,熱切地追索部落的樣貌、語言和祭典,用粗淺、浮略的方式。我想起壢坵的小米田、想起大港口的龍的故事,想起破碎的、片段的族語單字嚼在嘴裡:
原住民是甚麼樣子的?他們怎麼說話、怎麼想、用甚麼方式過生活呢?誰是原住民?
那,我是誰?
這股隱晦的身分認同思索,隨著我來往更多村落、參與原住民族議題更深(當然,至今我的認識仍太淺薄),開始蔓延開來,形成日常的焦慮,反反覆覆。
身為白浪,我很抱歉
在原住民面前,我反倒經常覺得自己蒼白無光、沒有文化,在遊行隊伍上,朋友們身上傳統服飾的叮噹聲,都讓我感到刺痛。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白浪,純純種種的白浪,甚至為此沮喪。
(下接第 2 頁)
編按
- 日治時期戶籍謄本「種族」欄位標記「熟」,即表示為「熟番」,亦為「平埔原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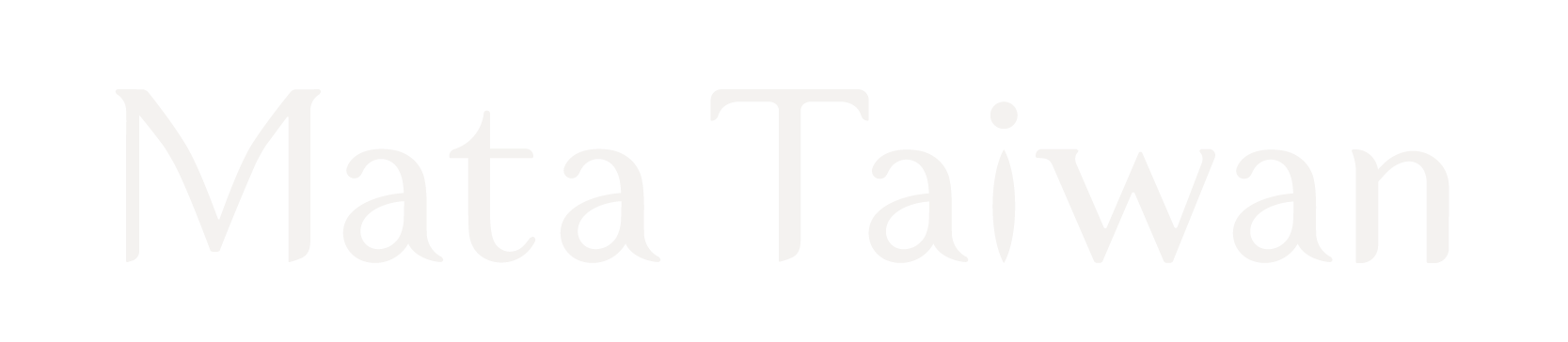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