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槍爭議懶人包沒說的事:獵人不再傳統,是否必然導致對國族的信仰?
布農族人 Talum(王光祿)因獵殺保育類的山羌,經判決即將入獄服刑,引發空前的關注與聲援能量。原訂今日(12/15)上午 9 點傳喚 Talum 到案,但下午全案出現轉機, 檢察總長顏大和針對此案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而最高法院檢察署在新聞稿提出了兩點,其實深具意義:首先,最高法院檢察署聲明認為「原審判決自行限縮解釋」,質疑原審判要求原住民自製獵槍之性能要符合「依照原住民文化之生活需要所製造」或「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的要件才能主張免責的解釋,其實隱含了族人日後皆不能再自製比以前祖先更精良的獵槍打獵,造成原住民族發展其特有文化之歧視,更違反尊重原住民發展的立法意旨。
二是針對違反獵捕野生動物的部分,以適用法律應從優從新之原則,應適用《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第 19 條規定,才是有利原住民之認定。
此外,高檢署也認為原審適用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並不符合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對原民的保障(編按1),而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作為有罪認定野有適用法不當之違法,因此提起非常上訴。
雖然最高法院檢察署今天做出了這兩點關鍵解釋,但對照這幾天針對狩獵的種種爭議與討論,我仍想嘗試不以法律解釋作為主要依據,而是透過重新推敲、界定概念的方式,談談關於狩獵,從部落到國家以後,為什麼問題變得這麼複雜。
第一個批判:所謂的傳統太浪漫
浪漫並無助於直面現實的殘酷,甚至挑起更多以傳統對抗國族戰爭的對立場面。
狩獵這件事,究竟自何時開始,從作為一種原來住民(在「原住民」一詞尚未誕生前)養活自己的重要方法,轉變成當今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族自治訴求中,被一再強調並賦予高度「傳統文化」意義的權利?
與大自然永續依存的狩獵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窺視下,該怎麼解決與動物保育或治安風險的矛盾關係,似乎一直被刻意忽視或轉移焦點。可是,無論心繫傳統的漢人如何站在一個純淨的位置上,奮力為文化的無罪辯護,卻恐怕仍是在增添一種「高貴的野蠻人」的浪漫色彩。
然而,浪漫並無助於直面現實的殘酷,甚至挑起更多以傳統對抗國族戰爭的對立場面。
尤其當聲援者呼籲國家要落實原住民族既有的自治權,往往招來更多評論與懷疑,認為狩獵文化如今在現代社會都難以維持,該怎麼去規範那些其實已經脫離部落自律系統的族人?難道在現代法律層面上是雙重標準?
若只訴諸於幾百年前就有的傳統文化脈絡,難免欠缺說服力,不過我在此憂心的卻是,太簡便地推導到國家的壓迫導致自治權被剝奪,似乎加深的僅僅是對於現狀的無力感;另一方面,甚至在快速流通訊息的臉書上,對於「不守法」的原住民強加的種種責難,也都在惡化族群之間的誤解情況。

狩獵議題引起爭議,也意外挑起原民傳統與國族主義者的戰爭。
空泛的傳統,如何與國家主義對抗
當國家為了有效維持、管理長期的政治經濟體系,便有必要擴展權力的觸及面向,以控制愈來愈複雜的風險問題。
一個需要被釐清的困境是,人們雖然知道當代原住民的確面臨國家介入,難以平反長期以來遭受侵略、剝奪的失語位置,但每當談論「傳統」卻淪於空泛、淺薄,無法更具體地說明究竟是什麼施力點,導致在今日的世界上,幾乎很難再有獨立於國家以外存在的政體。
邁向國家政體的發展過程,除了權力愈趨集中的大方向,其隱含的問題還包括,為什麼在人口密度更大、組成背景更複雜的情況下,也意味著獨立或自主性愈來愈困難?
因此若要把答案說得更精確一些,應該是國家如何因應前述情況,而產生一套掌控各種資源的策略。當國家為了有效維持、管理長期的政治經濟體系,便有必要擴展權力的觸及面向,以控制愈來愈複雜的風險問題。
而這些面向恰恰直接扣連到這次狩獵文化與法律的衝突關係,也就是「經濟」(仰賴什麼維生?)、「軍事」(為什麼要管控槍枝?)以及「意識型態」(合理化統治階層的基礎)。
政經權力被抽離,是部落失序的主因
當原有部落領袖被國家的中央或地方行政體制取代後,他們就已難以在部落發揮影響力,這之間更隱含了權力「菁英化」的傾向
首先在經濟上,我們必須意識到,與累積幾百年的狩獵傳統相比之下,近幾十年才有的生態保育意識,其實是相當晚近的價值觀。如今狩獵文化面臨消逝、難以傳承的危機,伴隨的是更大層面、從部落自我管控機制到個人在國家社會之中的「失序」狀態。
而原住民成為國家經濟體系下的邊緣角色,其實也是伴隨國家掠奪、宰制原住民既有的經濟資源而來 ── 愈來愈多族人因而被迫往都會區移動、找工作謀生,他們所面對的艱難,不但是與部落的關係愈來愈疏離,無法熟悉原鄉的語言和文化,也逐漸在社會迷失了自我認同的位置。
因此從行政體制來看,我們一方面要認知到,當原有部落領袖被國家的中央或地方行政體制取代後,他們就已難以在部落發揮影響力,這之間更隱含了權力「菁英化」的傾向(編按2)── 國家政府階層抽空部落傳統的內部律法脈絡,並重新定義哪些規範是合理的、哪些價值才是該被遵守的,導致一種荒謬的後果是:無論是「依法行政」還是「守法」,這種由特定優勢群體擁護的評論方式,理所當然地把「保育動物」看得比「保護獵人」更為重要。
另一方面要指出的誤解是,部落的自律性維持困難,不該是用漢人社會對「個人道德」的批判凌駕於部落之上。
原住民在臺灣社會長期以來經濟的自主性喪失,很遺憾地,似乎與傳統文化被膚淺構框的視角有著類似命運:把原住民的貧窮、失能歸咎於「個人不夠努力」,而非「生產工具或資源被國家剝奪」。
有了前述的認知基礎以後,我認為我們才能相對同理地去思考,傳統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延續的議題要處理的複雜性,並非單單去「要求原住民必須先自律」就能達成。
理解國家槍枝管控,也需理解槍的文化脈絡
寧願相信明文規定的強制性或有效性,也不信任部落內部自有的規範,這背後透露的其實是一種對於現代國家的信仰。
接著進一步討論槍枝的根本問題,究竟為什麼要管理槍枝?這要從「軍事」對於國家政體的關鍵意義來討論。
當國家為了捍衛國土、擴張版圖,軍事便不再停留在小規模的群體之間解決爭端的範圍內,而關係到更大規模的層次,對內控制社會治安、對外如何維持國家安全的條件上。槍支的定義或內涵因而受到體制專業化的影響,自然也抽離了狩獵的脈絡,直接支配整個原住民社會。
的確,獵槍既能是捕獵工具,也能是武器。但同時間,為何原運團體會提醒關注此事件的人,理解原住民文化與槍枝的脈絡也非常重要?
這是因為當你只是用當代國家對槍枝規範的認知,方便地去套用在法律難以釐清的灰色地帶上(如自製獵槍的爭議),就難免忽視獵槍如何被使用,與使用獵槍的人涵蓋的文化背景,兩者之間綜合起來是否足以適用現代法律解釋的問題。
如今加諸於狩獵的種種限制,正走向違悖「文化傳承」立法精神的路上,彷彿要迫使族人必須先讀懂中華民國的法律,再來學習部落的狩獵技藝。
可惜連日來,我看到許多質疑狩獵文化「合法性」的評論,似乎寧願相信明文規定的強制性或有效性,也不信任部落內部自有的規範,這背後透露的其實是一種對於現代國家的信仰 ── 相信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比起部落更大。但這種相信國家制定與落實的法律能夠帶來的保證,其要付出的代價,卻是原先個人或社群的自主性換來的啊!
如今人們相信法治對於社會安定的重要,也等於認同了國家透過教育、媒體等體制上灌輸特定意識型態的成功,不僅合理化長期國家經濟發展下將原住民經濟邊緣化的問題,使其不得不成為向國家伸手要補助的弱勢族群,在觀光文化發展上一再地將原住民視為表演性的道具,現在又以「不夠傳統」的狹隘判決認知將原住民獵人污名化。
我一直在想,非原住民可以在這些日子的狩獵爭議輿論之中學到什麼?我想有兩個:
一是我們至少要正視原住民觀點在中華民國法律是否得到應有的尊嚴與重視 ── 別忘了,無論在《憲法》、《原基法》及《聯合國兩公約》皆保障原住民族的自治權。
另一則是關於為什麼我這篇要從邁向國家的過程,來重新談狩獵爭議背後一些根本的問題。
我期望,藉此可以反省到今日我們生活的網路世界,大量的陌生人不得不接觸彼此,面對以前從未好好認識過的他者,處理自身偏見比較好的方法不該是仰賴自己原先有的常識,太快地被「懶人包」說服,掩蓋的不只是事件真實的面貌,也深深影響到不同族群之間正在以錯誤而令人心痛的方式想像彼此。
編按
- 根據《原基法》第 19 條及第21條第 1、4項所定「應經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而與原住民族共同建立管理機制」之特殊法規制定方式,與 2007 年 9 月 13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之《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12 條第 2 項、第 14 條第 3 項、 第 15 條第 2 項、第 17 條第 2 項、第 11 條第 2 項及第 19 條所定「基於遵重原住民族之自主權及自治權原則下,要求各國政府應在各原住民族知情、同意下,共同制定原住民族行為規範」 之宣言意旨相符合。
- 除了國家體制,其實宗教信仰組織在更早的時候傳入台灣民間,也從顯性至隱性改變部落的權力結構,換言之,對於部落政治結構的改變,除了國家力量影響之外,也還有其他原因待考量。

關於作者
Vanessa,讀社會學、人類學的大學生,關注性別政治文化、社會運動。每天都要喝咖啡,平均 20 秒讀完一篇網路文章,喜歡在不讀書的時候一個人去閒晃,聽故事,觀察路人和風景的變化,是一個持續練習寫字的人。
相關文章推薦
你也有原住民或部落的故事要分享嗎?
《Mata‧Taiwan》熱情徵文中!
也歡迎加入我們粉絲團,
每天追蹤原住民文化、權益大小事!
圖片來源:Vanes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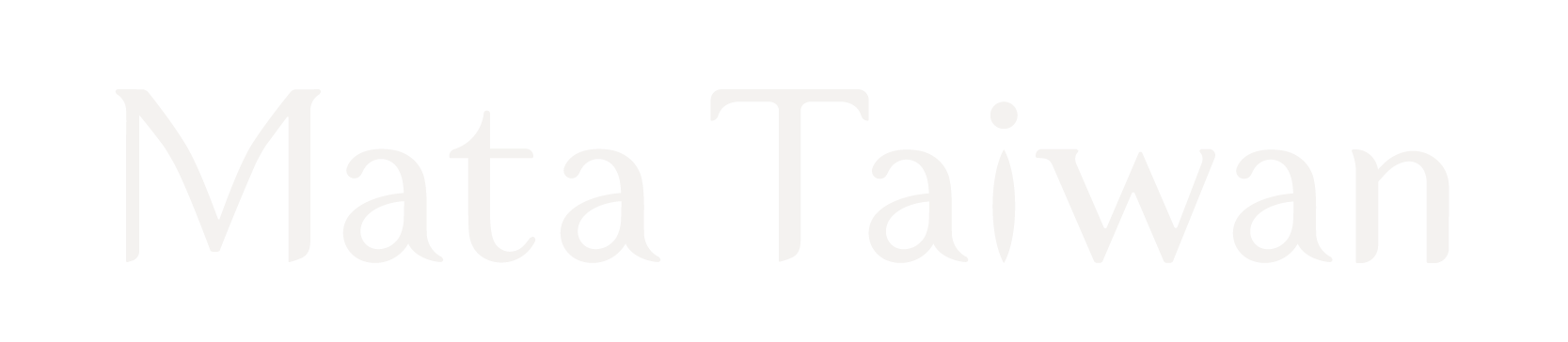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