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台灣不應只剩玉山,更要認識這座「東谷沙飛」
明天(7/15)《東谷沙飛傳奇》改編為舞台劇即將就要展演,我稍微有點小興奮而無法入眠,就像小時候明日即將遠足今晚失眠一樣。許多複雜的思緒湧上心頭,想起了許多事,也想起了許多事。
回顧這歷程,有時高峰也有時低谷,但我內心滿是喜悅與感恩,感謝這一路許許多多的朋友不同的陪伴與支持,也感謝台北兒童鞋子劇團團隊的看見與付出,更感謝天上的天讓我領受這諸多恩典。
我想起當初完成小說創作即將就要跟出版社簽約的當晚,我不知怎的該是愉快的夜,竟陷入了天人交戰的煎熬之中,我突然好像站在民族歷史的轉折,背負著一種民族命運,在十字路口上徘徊難行;我的煎熬是在於因著小說的需要,我大量地改編了神話傳說的內容,我擔心將來有族人控訴我改變了、扭曲了我民族傳說故事,而我又要如何面對我列祖列宗?
我嚎啕大哭,無法自己,所幸我也在當晚得到了釋懷,我告訴自己:我是 Bunun(布農)(編按1)的孩子,我有這一份權力、責任與身份繼續說我先祖的故事在現在,讓它在現代產生意義、價值與力量,指引我前面的道路!
鵪鶉背石上山的故事,是我對民族傳說的啟蒙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從此我的腦袋被顛覆,開始認知了民族傳說故事的一種真實性,乃至於它們所傳達的關於我民族獨特的自然觀,以及我們存在的世界觀想像。[/epq-quote]我也想起來 28 歲那年跟著部落耆老 tama Bali 走回中央山脈老家時,半路上老人家突然大喊:
“Siadik a batu enaman’i mumu a……”
(就是這顆石頭,鵪鶉鳥背上山的啊⋯⋯)
我從小就知道我們有一則關於鳥類比賽背石頭上山的故事,但一直都覺得那只是像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話一樣,天馬行空、杜撰,只是拿來給孩子說說的故事,不可能為真。
然而那天我竟走著走著就遇見了傳說,我走進了神話故事的現場,神話故事竟就這樣真實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非常震撼,像是被雷擊中一樣,真假失去了界線,久久無法回魂 ── 後來我仔細端詳那石頭,還真的那是屬於河床的石頭,不是山上的,並且因為鵪鶉鳥背的時候是用頭背袋綁著上山,因此石頭身上還有一道繩子綁著很深的溝痕。
從此我的腦袋被顛覆,開始認知了民族傳說故事的一種真實性,乃至於它們所傳達的關於我民族獨特的自然觀,以及我們存在的世界觀想像。
布農世界裡的玉山,是東谷沙飛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Pa qada paun epi tu Tongku Saveq, opa maszan tu laningavan dengaz ka tinpaqtinpaq!” 難怪這山叫做東谷沙飛……[/epq-quote]也在當時,我第一次登頂台灣第一高峰玉山主峰。
我家就住在可以直接眺望玉山的望鄉部落,這山叫做「玉山」── 我一直以為這是一件天經地義、自然而然、不是問題的問題。然而那一次冬初寒流來襲、霧氣茫茫,什麼也看不到,我們彷彿置身在一座孤島一樣,四周都是可怕的浪濤,見此風景一位長輩說道:
“Pa qada paun epi tu Tongku Saveq, opa maszan tu laningavan dengaz ka tinpaqtinpaq!”
(難怪這山叫做東谷沙飛,因為這就好像大洪水氾濫一樣,滾滾翻騰啊!)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原來這山叫做「東谷沙飛」!
這同樣讓我震撼,也開啟了我不一樣的民族視野、價值與認同,我甚至認為這些故事蘊含隱藏著關於我民族的認同與歸屬的價值,這也啟動了我的東谷沙飛意識,也啟動了我從文學創作乃至於文化工作的「東谷沙飛運動」。
從「玉山學」到真正屬於台灣的「東谷沙飛學」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就連我們的聖山也都被殖民了,它只剩下「玉山」這個名字,於是我認為我們必須要解放台灣第一高峰。[/epq-quote]從那時候我展開了從文學創作、部落工作、乃至於登山健行的「東谷沙飛運動」。首先我意識到台灣人很想要讓玉山成為台灣的聖山,我認為這背後有著一種去中國化的意義,也就是想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新的認同,於是想封玉山為聖。
這樣的聖山運動在台灣大概推動了將近 20 年之久,之後產生了所謂的「玉山學」。意思是生為一位台灣人就要認識玉山,要認識玉山就要爬玉山,爬玉山成為認同台灣的一種方式,這就興起了一波台灣人想要爬玉山的文化運動,即:作為台灣人一生就要爬一次玉山;其次因為玉山是台灣(東北亞)第一高峰,它高、美….. 所以是台灣的聖山。
台灣文藝界人士透過藝術、文學等方式企圖要封玉山為聖,甚至歌手林志炫還唱了一首《玉山之歌》,唱得比《中華民國頌》還要雄偉,2011 年玉山國家公園還想要依此脈絡推動玉山成為七大自然奇景,但就是力氣不足。
原因是背後沒有足夠的故事、理由讓玉山自然而然的被世人視為聖山;再來就是種種的運作也都嚴重忽略了在地部落與山之間的關係 ── 而這種忽略也同樣發生在在地的部落社群當中:族人不再述說這些故事,也因此喪失了這些故事背後所蘊含的生態智慧,乃至於喪失了某一種關於人與自然獨特的理解與詮釋權,這是族人的損失,也是台灣的損失。
尤其我們說「殖民」這件事,就連我們的聖山也都被殖民了,它只剩下「玉山」這個名字,於是我認為我們必須要解放台灣第一高峰。
這便也是我為何會書寫這麼一部小說的重要理由,一是向社會大眾分享這山不只是玉山,古老以前這山叫做東谷沙飛(Tongku Saveq),她背後的大洪水傳說述說著人與自然神聖的交往,東谷沙飛是洪水災難中最後的避難所(編按2)。二是喚醒部落族人乃至於台灣第一高峰的東谷沙飛靈魂,因為我們似乎遺忘了聖山,聖山也遺忘了我們。
我認為東谷沙飛之所以為聖,除了神話傳說的價值之外,最核心的理由是因為 asang(家園)。

台灣原住民的傳奇故事足以媲美歐美的神話傳說,甚至更為豐富、精彩、多元,是有血有肉的東谷沙飛世界。(圖片/Neqou-Sokluman)
東谷沙飛,台版有血有肉的魔戒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我認為東谷沙飛之所以為聖,除了神話傳說的價值之外,最核心的理由是因為 asang(家園)。[/epq-quote]《東谷沙飛傳奇》在 2008 年由印刻出版,當時提筆寫作我便勵志要寫就一部台灣版的魔戒,因為我很自信地認為台灣原住民的傳奇故事足以媲美歐美的神話傳說,甚至更為豐富、精彩、多元,是有血有肉的東谷沙飛世界,不是架空的中土世界;我甚至也很自信的認為,將來有一天我這部小說會被改編成電影,於是我的文字、敘述、想像都朝著這個目標運作。但誰知當書本出版之時,除了得到 2008 年吳濁流文學獎之外,就完全石沉大海,沒有掀起任何的波浪。
沒想到經過了幾年的浮沈之後,這本著作終於被台北鞋子兒童實驗劇團看見,幾番溝通了解,甚至還遠赴山上部落,感受部落文化氣息、文學地景樣貌,便著手戲劇的計畫。
更沒想到的是,明日還真的就要搬上舞台了,從想像化為文字成為小說再從文字化為具象的舞台呈現,這讓我不禁要大聲讚美天上的天的恩典與祝福。
明日我將帶著我的家人,部落那裡也將有一部大巴士帶著將近 40 位的小朋友北上觀賞來自自己家鄉的《東谷沙飛傳奇》,除了舞台劇的改編,最讓我欣慰的也是這些事。
因為寫作是孤獨的,文化的實踐更是孤單,沒有多少人可以真正認知一位文化實踐者的思維是什麼,於是路途上經常有非議、不被理解與不被認同,而如今這些事情得到了實踐也得到了突破,也看見了延續與傳承,並期待明天。
感謝天上的天,也感謝我的朋友們!
編按
- Bunun:布農族人的自稱,但在布農族人接觸外族前,bunun 即指「人」,而在布農族原始的宇宙觀中,世界由 bunun(人)、hanido(精靈)與 dehanin(神)所組成。
- Tongku Saveq:布農族人稱玉山為 Tongku Saveq,tongku 指山頂斜坡,saveq 或 savih、usavih 則是布農族人口傳遠古祖先「最後避難之地」,與布農族的大洪水傳說有關。
延伸閱讀
關於作者
Neqou-Sokluman(乜寇.索克魯曼),南投信義鄉望鄉部落布農族人,詩人、小說家,同時也是一名高山嚮導,創作充滿布農民族情感與文化生態價值。
愛原住民?想關注、參與更多部落大小事?歡迎:
追蹤:為我們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分享這篇文章
分享:將您對部落議題的想法寫下來,或分享部落活動
參與:看看我們推薦的部落好物,用行動支持部落產業
主圖來源/林 軍佐,CC Licen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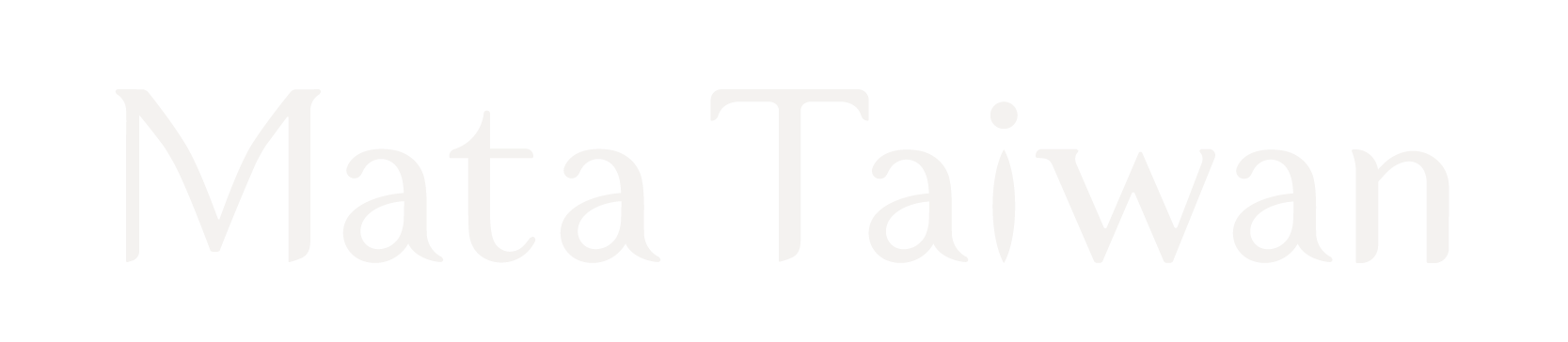



莊富安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38151999536649&id=100000255834611
我想作者該看一下這個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