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被歧視而說漢語」阿美族金鐘主持人阿洛:我曾覺得說母語是可恥的事
週六午後,提早半小時來到活動現場,隨工作人員指示將椅子圍成一大圈,一邊聽阿美族歌手 Ado’ Kaliting Pacidal(阿洛.卡力亭.巴奇辣)跟樂團排練。
「Oh oh hay yan! Oh oh hay yan!」看 Ado’ 身體自由擺動輕鬆地哼著歌,可以預期 Ado 將在接下來這 3 小時,讓觀眾感受到同樣的心情。
主持人孟純簡單開場後,按照「哲學星期五」的慣例,每一位觀眾會輪流自我介紹 ── 但今天卻特別不同,Ado’ 說:「我要教大家阿美族的方法,用唱歌來自我介紹。」她示範唱著:「Gee~Ado’! Gee~Ado’! Gee~ Ado’! Gee~ Ado’!」她唱完後,其他人必須重複兩次「Gee~ Ado’」,表示將祝福送給這位自我介紹的人。
Ado’ 說:「每一個人都要試試這樣的方式。」現場起了一陣騷動,不少人臉色微微不自在,甚或有些人躲到後排座位去。「阿美族的神話說,人類生下來就該唱歌的,不愛唱歌的人,你們是不是常常胸口悶悶的,可能會有呼吸道的疾病喔!」現場一陣大笑。於是 Ado’ 拿著麥克風走過每一位觀眾,帶領大家自我介紹,不時抽問觀眾說,剛剛自我介紹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儘管聽得出來很多人不常於大庭廣眾前唱歌,有些發顫走音,但走過一圈後,現場氣氛也漸漸地輕鬆自在起來。
Ado’ 演唱一首歌後,一位領養阿美族男孩的美國母親問道,如何讓她的孩子在海外能接觸阿美族文化以及語言?那位母親說小男孩過於害羞不敢現身,希望 Ado’ 在活動結束後可以跟他私下碰面。「沒關係,這是正常的,阿美族的男生本來就比女生害羞。」Ado’ 笑答。Ado’ 表示現在網路上有許多影片,她在原住民電視台也有主持節目,皆是很方便的資源,「其實我自己也是長大後,再度學會說阿美語,這會是個很長的故事,大家想不想聽?」全場觀眾異口同聲地說當然想聽!
與 World Music Ensemble 合奏。(Credit: Chia-Chun Chung)
「我曾覺得說母語是可恥的事」
「我上小學以前一直以為全世界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阿美語;上了小學後,才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語言,漢語(北京話)。」
上課第一天,老師要全班同學輪流上台介紹自己,卻不是以 Ado’ 熟悉的方式和語言,濃濃的原住民腔漢語,更成為全班的笑柄,班上男同學在下課後繼續模仿 Ado’ 的腔調嘲弄她。
那時還不懂得「霸凌」和「歧視」這兩個詞的 Ado’,經歷這樣的事件後,下定決心要學好漢語,死記硬背老師發的演講比賽的講稿,獲得代表學校出賽的資格。卻仍有同學質疑:「老師,Ado’ 根本不是中國人,是山地人,憑什麼參加比賽?」Ado’ 示範當時如何比賽,當她以字正腔圓地語調說出:「校長,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 ── 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全場都被逗樂了。
但 Ado’ 說:「從那時開始,我覺得講母語是一件很可恥的事。」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我上小學以前一直以為全世界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阿美語;上了小學後,才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語言,漢語。[/epq-quote]Ado’ 把精力完全投入學習漢語,成功地考取中文系。可是她再不說阿美語了,即使回去探望外公外婆,仍以漢語回答他們。
Ado’ 那時心裡想:「如果說著跟漢人一樣流利的漢語,能夠站在台上以漢語演講,那些歧視能否就此消失?」
抱持這樣的想法直到大學一年級,Ado’ 因外公過世而回去奔喪。喪禮結束後,Ado’ 想用阿美語來安慰不懂漢語的外婆。她想對外婆說:「外婆,我馬上要回台北念書,妳不要太難過,好好保重身體。」Ado’ 想,這簡單的幾句話,縱使很久沒講,應該沒問題。但要開口的瞬間,她想不起這些話要如何用阿美語表達,最後,結結巴巴地留下一句:「我要回台北了。」
Ado’ 在客運上一路哭著回到台北,她說,那時外婆一定難受至極 ── 從小無話不談的孫女,居然再也不願用阿美語溝通。
Ado’ 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是誰,偶然讀到法國黑人哲學家法農(Frantz Fanon)所著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書中一句話引起 Ado’ 共鳴:
「當我講著流利的法語,我突然覺得自己的膚色變白了。」
從「林佩蓉」回到「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當我講著流利的法語,我突然覺得自己的膚色變白了。[/epq-quote]從荷蘭西班牙一直到清朝日本國民黨政府的殖民,原住民被稱作次等的「生番」、「高山族」、「山地同胞」;恐懼殖民者,而強迫自己去學習熟稔他們的語言,或許是以說阿美語為恥的深層原因,Ado’ 如此說著。
身為原住民是件值得驕傲的事,她重新拾起阿美語,不再以為恥。彼時原住民運動正興,Ado’ 加入街頭抗爭的行列,1994 年原住民正名運動成功,原住民從此不再被稱呼為山地同胞,身分證上也可使用族名。Ado’ 從「林佩蓉」恢復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Ado’ Kaliting Pacidal)。
這時觀眾問:「妳的名字代表什麼意義?」Ado’ 說:Kaliting 是她母親的名字,而 Pacidal 意謂太陽,表示他們是奉太陽為守護神的氏族。「Ado’ 這名字的由來是個很長的故事,想聽嗎?」Ado’ 笑著問,大家仍是相同熱烈的回應:「想!」
很久以前,阿美族祖先和天神起衝突,天神一怒下起暴雨,村莊氾濫,村中長老拜託一位名叫 Ado’ 的年輕女孩,請求她去安撫天神。於是 Ado’ 站上村中最高的山丘,對天神開始唱歌,唱啊唱啊,不停歇,天神最終被她的毅力感動,停止這場暴雨。
Ado’ 說:「我的長輩替我取了這個名字,並不是希望我很會唱歌,而是期許我能做一個堅持不放棄,善良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以音樂代替街頭倡議
有感於族裡的年輕人不再講阿美語,聚會中皆放著日韓的流行歌曲,Ado’ 開始以阿美語填詞,譜上流行音樂的曲風。音樂是一個能帶動流行的媒介,Ado’ 笑著說,我想扭轉年輕一代的想法,說阿美語可以是一件很 fashionable(流行)的事。她拿出一張不久前發行的電音單曲,封面是她一頭藍紫色短髮,眼睛周圍與臉頰上點綴黑色圖騰的刺青,「這樣是不是有 Lady Gaga 或是 Rihanna 的風格?」全場大笑。
有時在唱片行還會看到這張專輯被歸於西洋流行音樂區,曾走在街頭抗爭的最前線的 Ado’ 嘶聲竭力地喊著:「恢復我們的母語!」但她發現,這張電音單曲帶來的影響力,比街頭抗爭大多了,她說:「我現在不斷告訴自己要有自信,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大家覺得原住民音樂不時尚沒關係,我來做引領潮流的那個人。」
有觀眾建議是否考慮嘗試一曲兩詞,阿美語和漢語,或許可以擴大歌曲的流行程度?Ado’ 答道,她並不介意填漢語歌詞,英文也無妨,都不會改變歌曲蘊藏的精神,但她說,漢語與阿美語的音節組成方式很不相同,阿美語其實與英文比較接近,「阿美語講快一點其實也很像法語喔,再次證明阿美語是 international language(國際性的語言)!」Ado’ 逗著大家。
填兩種詞會需要譜兩首曲子,等於創作兩首不同的歌,那便失去一曲兩詞的本意 ── 而更深一層的考量是,阿美語或終將消失,如能趁現在多創作幾首歌曲,當作阿美族留給這個世界珍貴的禮物吧,Ado’ 淡淡地說著。
牽起手,給彼此力量
中場休息後,Ado’ 又表演了幾首歌曲,讓人印象最深的,歌名叫《Pasiwali》(意譯:望向東方),講述二戰時被日本強迫派到前線的阿美族年輕人,知道當第一束光線從東方出現之際,必須向他父母與故鄉告別;他知道無法抵抗命運的安排,請他爸媽不必為他擔心,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Ado’ 嘹亮的歌聲在鋼琴、吉他、大提琴、塔布拉鼓(tabla drum)及合唱團的伴奏中,傾訴無可奈何的心境。「現在開始我要教大家唱歌跳舞啦!」Ado’ 活潑地說道。首先是一首 Ado’ 只花 10 分鐘寫成的歌曲,背景是小時候 Ado’ 受傷時,她爸爸總會指著 Ado’ 的傷口說:「Oh oh pushh!」一邊以手在她傷口上方虛捏像是捉起一把沙子,然後向一旁灑出,她爸爸會問:「妳現在還痛嗎?我已經把妳的疼痛轉移走啦!」當 Ado’ 感到沮喪難受時,想起她父親這樣的方法,於是有了這首歌:
「Oh~ Oh~ Hay yan~ Oh~ Oh~ Hay yan~
Oh~ Oh~ Hay yan~ Oh~ Oh~ Hay yan~
Hay yan~ Hay yan~ I yan~ I yan~ Hay yan~
Hay yan~ Wuuuuuuu~
I yan~ I yan~ Hay yan~」
學會這首歌後,大家圍成一圈,兩手分別和相隔一人的人牽手,如此一來,相鄰的兩個人便會肩併肩,「這樣牽手的方式,可以讓我們更貼近兩旁的人,感受身邊夥伴的律動步伐歌聲呼吸,給予彼此力量。」
Ado’ 擔任領唱,並解釋接下來的歌曲意涵:阿美族歌曲中有很多對唱的歌曲,擔任領唱者是負責祈福的人;答唱者則將力量借給領唱,幫助他祈福。接著便是三首對唱歌曲,一群來自台灣、美國、印度等不同國家的人,一邊踩著步伐,一邊應和 Ado’ 的嗓音,「有人的嘴巴還張不夠開喔!」Ado’ 不時開玩笑地提醒:「阿美族憲法有規定,唱歌時身體必須跟著擺動,請不要違法!」
「不要管旁邊的人怎麼跳怎麼唱,自由發揮走出自己的路!」Ado’ 喊著,現場有如慶典的氛圍,結束後每個人都汗流浹背,但一開場那拘束憋扭的氛圍已悄無聲息地消失,多久沒有放鬆地擺動身軀,大聲唱歌,不在意安全距離地與陌生人如此貼近。
最後 Ado’ 感謝道:今天很高興能以最擅長的方式,舞蹈和音樂,與大家對談,謝謝大家熱情地用歌聲舞步回應她,「阿美族祖靈一定沒想到,有一天祂們的音樂舞蹈會律動在波士頓。」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當哼起母語的歌曲,我們重新記起了自己是誰,從何而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家。[/epq-quote]回程在地鐵上,口中不由哼起:「Oh~ Oh~ Hay-yan!」Ado’ 說,希望這首歌能撫平傷痛,安慰每個在城市打拼的靈魂;而我想著,母語對人類而言到底是什麼呢?是在嗷嗷待哺時期,母親用來安撫嬰孩哼頌的語言吧。
而之所以會莫名地感到痛苦悲傷,是不是因為忘記了母語,忘記了用來撫平傷痛的語言,所以感到不安,感到傷口無法癒合的焦躁?
但當哼起母語的歌曲,我們重新記起了自己是誰,從何而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家。
「I-yan~ I-yan~ Hay-yan!」
(本文原刊載於《Café Philo @ Boston部落格》,原標題為 <遇見阿洛 ─ 我的母語,我的音樂,我是誰>;聯合主辦單位/Dudley World Music Ensemble at Harvard、哈佛台灣同學會、波士頓哲學星期五;文字/Ching-Huan Chen;攝影/Chia-Chun Chung。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但當哼起母語的歌曲,我們重新記起了自己是誰,從何而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家。」(Credit: Chia-Chun Chung)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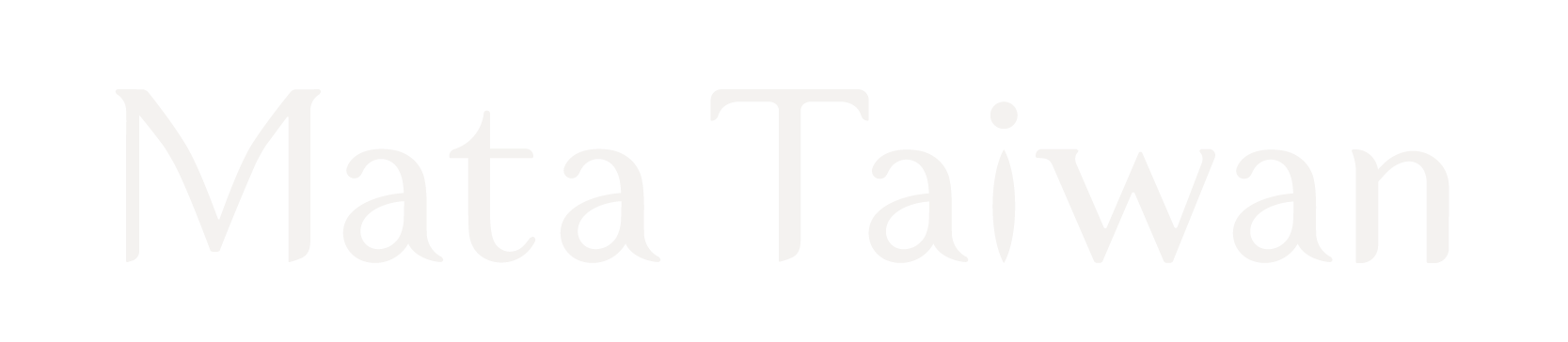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