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你的「愛台灣」可能加了不自覺的種族歧視!那些社會學偷偷從人們看到的種族主義
我上課的時候會問學生以下問題:「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1)黑人/非裔美人,(2)白人,(3) 印尼人。」大多數的同學露出「老師,這問題太簡單了吧」的表情,回答當然是(1),少數反骨同學懷著「其中必有詐」的揣測說是(3)。曾經有一位很兩光的同學說是(3),誤以為歐巴馬在印尼出生。
偶爾,有人舉手問:「可以有一個混血(mixed)的選項嗎?」
沒錯,歐巴馬是黑白混血,爸爸來自肯亞,媽媽是美國白人。那麼,為什麼人們,包括媒體,都理所當然地將他分類為黑人?
這個謎題揭露了:種族不是客觀、本質性的生物分類,而是歷史建構的、簡化的社會分類。
歐巴馬被「種族化」了
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歐巴馬被「社會建構」為黑人:首先,因為我們習於從父親來界定子女的族群身分,反映出父系優先的親族秩序以及家庭內的性別權力。
那麼,如果歐巴馬的父母倒過來,變成白人爸爸、黑人媽媽的組合,他是不是就會被界定為白人呢?我想也不會,原因在於黑白的種族分類不是平行的類別,而是階層的高低。
美國在黑奴時代曾用「一滴血政策」(one-drop rule)來界定人們的種族,只要你的基因庫裡有非白人的血統,你就不能被認定為白人。由於當時有許多白人領主與黑人女傭生下的孩子,他們不會依父系原則被認定為白人,而是按照一滴血政策被歸類為有色人種。越強勢的族群,越有權力來畫定與捍衛界線,以保障特權與資源的佔有。
最後,膚色等外形差異其實是連續分佈的光譜(比方說,黑中帶白、白中帶黑),然而,社會建構的種族分類是互斥、甚至二分的類別(非黑即白),其間的界線不容踰越或混淆。
來自牙買加的文化理論大師 Stuart Hall 曾經說過:「我在英國變成了黑人。」他的母國有著複雜的殖民與移民的歷史,當地人們會依據膚色的樣態、血統的混雜分成十多種細緻的分類,到了英國留學後,人們卻只喊他「你,黑人!」,從此烙上被歧視的他者身分。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種族不是客觀、本質性的生物分類,而是歷史建構的、簡化的社會分類。[/epq-quote]「種族」(race)作為一個名詞,產生的「社會誤認」效果是,讓人們以為種族分類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既然被視為「自然」的事實,那就不可改變、無庸置疑,也強化人們對越界通婚或混種後代的恐懼。
當今的社會學界轉而使用「種族化」 (racialization)的概念,藉由動名詞來強調種族區分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 更確切地說,種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一族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不僅忽略了該群體內部的異質性,也放大了該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界線鴻溝。
種族主義是什麼?
2012 年 2 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有個 17 歲的黑人孩子 Trayvon Martin,穿著一件戴帽 T(hoodie),跟父親到一個有保全管理的社區去找朋友。嘴饞的他繞去超商買果汁糖,遇到了 George Zimmerman,一個西班牙裔的白人,也是該社區的守望相助隊員。Zimmerman 看見這個把手放在口袋裡的黑人孩子,衍生猜疑與恐懼—這個外來者闖入我們社區幹什麼?口袋裡藏的是槍還是毒品?他以「正當防衛」之名開槍殺了這個孩子,斑斑的血跡滴在口袋裡屋鮮豔的果汁糖上。
2013 年 7 月佛羅里達法庭宣判,缺乏種族多元性的陪審團判定 Zimmerman 無罪開釋,在全美各地引起譁然與抗議。歐巴馬總統在事件發生後語帶哽咽地說:「Trayvon Martin could have been my son.」(如果我有兒子,也可能發生類似的遭遇)
以上的故事,跟另外一個概念「種族主義」有關,這個觀念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影響我們如何認知他人以及進行人際互動,例如那個白人 Zimmerman 認定黑人「一定是那個樣子」,所以他必須「正當防衛」(編按1)。
所謂「種族主義」,是指伴隨著前面說到的「種族化」過程中,弱勢的群體,不僅被看成共享自然本質的集體,也被再現為必然劣等,相對於優勢群體有著不可消弭、無法共存的差異。這個概念要強調的是,種族歧視不單純是個人的偏見(只是壞心眼的少數人),而是建制化、系統性的社會關係(多數人有意識或無心地參與其中);這樣的結構體制,透過文化與知識的生產、國家政策與社會制度的訂定,持續再製、強化種族的階層分類,影響到不同人群在機會與資源上的不平等分配。
我們在日常互動中,往往對「他群」(與我們不同的人)抱持種族化的刻板印象。「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這個概念指的便是人們會用簡化資訊來假定某個種族的特性,執法者便依此對此群體提高警覺或加強調查。統計發現,美國的黑人男性被警察無故攔下的機率遠高於其他族裔;在反恐的氛圍中,中東或穆斯林人士在通過機場海關時容易受到盤查或搜身。
即便是透過教育與社會流動攀爬上地位階梯的黑人男性,仍無法避免「種族貌相」導致的歧視待遇。例如,2009 年 7 月,哈佛一名黑人男教授 Henry Louis Gates 要進入自家公寓時,因為鄰居報警「有黑人男性闖入」,竟然遭到逮捕。
台灣有種族主義嗎?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仍然掙扎面對社會空間與文化權力的邊緣化,並時時對抗隱形的種族歧視。[/epq-quote]行文至此,似乎都是發生在外國的例子,你或許在想:台灣有種族主義嗎?讓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湯英伸是在阿里山部落長大的鄒族孩子。他曾經就讀嘉義師專,但無法適應學校的軍訓文化而休學。1986 年,時年 18 歲的他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9 天後竟殺害了僱主一家 3 口。根據週遭同學所述,湯英伸是個純良的山地青年,為什麼他才到都市短短幾天,就變成殺人兇手?—— 因為他受到仲介業者的欺騙與敲詐,雇主強制他每天工作 17 小時以上,不時羞辱其為「蕃仔」。湯英伸想要辭職,卻被雇主扣留身分證不還,不僅沒領到工資,還要被扣留押金。
湯英伸一時情緒失控犯下罪行,雖然社會各界呼籲槍下留人,湯英伸終究成為臺灣最年輕的死刑犯。
在我成長的 1980 年代,原住民仍是一個族群的污名。上電視參加歌唱比賽的高金素梅只說自己是姓金的外省子弟,掩飾淡化了母親的泰雅族背景。
原住民的資源分配與社會地位至今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在特定的場域,如歌唱與運動,原住民的表現更甚漢人,雖然這也成為新的種族刻板印象。在「新台灣人」國族認同打造的過程中,原住民被納入「四大族群」的論述中,甚至在象徵的層次上取得代表性位置,比方說,國際參訪的台灣團,多透過原住民服飾與文化來突顯台灣與中國的差異。然而,原住民的核心地位僅僅停留在象徵的層次,甚至流於膚淺展演、錯誤妝飾(註1)。
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仍然掙扎面對社會空間與文化權力的邊緣化,並時時對抗隱形的種族歧視。—— 原住民舞者布拉瑞揚在 2013 年租房子時,房東在電話裡問他:「你是原住民嗎?」,布拉瑞揚歡喜地回答是,對方隨即說「我不租給原住民!」便掛掉電話。
我在進行外勞研究時重讀湯英伸的故事,驚訝地發現他的遭遇與外勞有許多類似之處:被仲介剝削、被雇主控制、被視為野蠻人、扣留護照與押金、不自由的勞工。
隨著原住民被納入「新台灣人」的內涵之中,「外勞」與「外籍配偶」成為「新的種族他者」,淪為社會歧視與經濟剝削的主要對象。
低劣的種族他者
隨著國際遷移的頻繁與擴大,外國人—政治文化社群的外來者(outsider)—經常成為種族化的主要目標。然而,並非所有移民都面臨同樣程度或形態的種族化;比方說,主張管制移民的法國右派人士,指的移民通常是膚色深的阿爾及利亞人,而非實際上人數較多的葡萄牙人。
這樣的現象呈現出:某些群體被認為具有歷史或文化上的親近性,可以變成「我們」的一部份,而其他群體被標舉出有根本差異,是不可同化的永遠「他者」。
種族同質性相對高的台灣社會,在 1990 年代初開放東南亞外勞之際,曾引起相當的焦慮與恐慌。當時的勞委會主委趙守博有以下發言:
「開放外籍勞工進口,很可能變成變相移民,我們到底能不能容納外來移民?能不能和外來勞工一起生活呢?我想,如果我們調查願不願意在台灣有泰國村、菲律賓村、馬來村,讓這些外國人跟我們分享我們這裡的就業機會和所有的一切,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同意。」 (註2)
趙主委對接納外勞的保留態度,建立在幾項未明說的假設上:一、東南亞外勞來自落後國家,必然會想要移民享受台灣的先進生活;其二、移民不是勞力與資源的提供者,而是機會與福利的掠奪者;其三,他們沒有辦法被成功整合與同化,將會以隔離的方式居住與生活,衍生種種社會問題。
台灣的社會新聞以及台灣民眾的觀感,特別是引進外勞的初期幾年,充斥了種族歧視的刻版印象。一方面,把外勞母國的經濟弱勢,歸咎於基因、氣候等「不可逆轉」的因素,如有台灣雇主把菲傭的偷竊解釋為因為菲律賓人是「海盜的後裔」,或認為這些國家的低度發展,實源於熱帶地區的人太過懶惰。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弱勢,又被認為是導致其人民在品格與習性上「難以避免」的缺陷,例如,女性移工被污名化為進行「假打工、真賣淫」,會為了逃脫貧窮而出賣肉體。
地方新聞也屢屢報導荔枝被偷採、雞禽豬隻遭竊的事件,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遭竊的農民往往指控或暗示外勞為嫌疑犯,認為這麼便宜的東西只有外勞才會偷。
2013 年 5 月發生的菲律賓警衛隊槍擊台灣廣達興漁民事件,不僅引起台灣與菲律賓兩國政府之間的對立與緊張,愛國主義的情緒發酵更挑起了台灣社會種族歧視的神經。菲律賓移工與移民在「悍衛國族尊嚴」的氣氛中遭受魚池之殃,各地傳來一些零星但駭人的歧視事件,如彰化有市場店家發起拒賣菲律賓人運動,張貼「我家的豬肉不給『非人』吃,請不要槍殺我」標語,也有因打工或婚姻來台的菲律賓人在街上被毆打或遭辱罵。

台灣的愛國主義,參雜了嚴重的種族主義歧視。(翻攝自東森新聞)
在這些事件中,我們看到「種族化」的運作邏輯:其一,菲律賓人被概括視為一個同質的群體,把開槍的警衛與買菜的菲傭混為一談;其二,菲律賓人的民族性被本質化為「野蠻的海盜後代」,所以,「非人」的對待之道可以被合理化;最後,基於「低劣的種族他者」的預設,台灣政府與民間因而對菲律賓政府的道歉感到「誠意不足」或「姿態過高」,也反映出台灣在世界體系中不高不低,又身為非常態國家的集體焦慮(註3)。
優越的種族他者
回到趙守博的發言,如果將其文字更改為:「如果我們調查願不願意在台灣有荷蘭村、日本村、美國村」,我想,恐怕有許多人會熱情地擁抱這些具有異國風情的村落。台灣的恐外論述指向東南亞社群,但台灣人鮮少對來自日本、歐洲、北美的移民產生類似的焦慮。
台灣媒體多將淡膚色的白領移工稱為「外籍人士」,「外勞」的說法僅指涉東南亞藍領移工,彷彿只有前者才具有完整而立體的人格,而後者卻被化約為單向度的勞動力。
我曾經訪談了近 20 位居住在台灣的西方移民,有關他們在台灣工作與生活的經驗。多數人都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好客,但也意識到自己身為外國人無時無地都受到異樣眼光。不同於在台的東南亞外勞,白人的他者身分往往可轉換為禮遇與特權,可稱之為正向的種族主義(positive racism),例如,在郵局或銀行可以得到優先服務、逛街時店員主動奉上 VIP 卡等(註4)。
訪談中最常被提到的就是摩托車與警察的故事,尤其是教英文的老外,由於沒有台灣的駕照,經常發生類似以下 Frank 的遭遇(現居桃園、與台灣人結婚):
「有一次我們被警察攔下來,我老婆就說,這駕照是紐約的,紐約的駕照是國際駕照,全世界都通用。現場有兩個警察,一個說:『ㄟ我沒聽過。』另一個回說:『吼,你沒聽過喔?』有時候,我被攔下來我老婆不在,因為我不會說中文,警察就得跟我說英文,他們很挫折,只好比手勢說:『Go, Go, Go!』因為他們沒辦法跟你溝通,他們覺得很尷尬。」
試想像如果台灣警察攔下的是一名騎摩托車的泰勞,他是否會對自己不會說泰文感到汗顏?或者相信曼谷的駕照是全世界通用?
以下 Patrick 的例子更鮮明地突顯了「優越他者」的地位,他也是娶了台灣老婆的美國人,目前與太太共同致力於環保教育的工作。當學校等機關邀請他們演講時,往往偏好邀請中文不很輪轉的 Patrick;當他們向政府或基金會提案時,朋友也建議由 Patrick 來說明,可能增加他們得到資助的機會。
Patrick 堅持用中文接受訪問,皺著眉頭地反省著自己在台灣的位置:
「有時候人比較會聽我的意見,只是因為我是白色皮膚還是什麼,就是又讓我喜歡又讓我討厭⋯⋯ 有些教授請我去跟他們的學生講課,這個在美國不可能的,這個在美國我可能沒辦法,因為我沒辦法跟其他人競爭,我的口才很差,我的解釋很差,不過在台灣,我突然變得⋯⋯」
坐在一旁的台灣太太有點無奈地補充說:「他們會指定外國老師,就是看外國人還是比較愛地球,或是外國人都是比較環保啊,比較愛和平。」
在這裡,我們再度看到「種族化」類似但不同的運作:西方人或白人被概括視為一個同質的群體,基於其母國經濟的先進發展,被冠上了文化光環,連結到現代性的價值與生活方式,如環境主義,即便 Patrick 的母國在許多環保議題上其實有相當負面的紀錄。
處於半邊陲的台灣人,在抬頭仰望白皮膚的「優越他者」的同時,複製了殖民之眼的凝視,低頭蔑視膚色更深的「低劣他者」。

台灣對待東南亞來的外國人,跟白色人種的外國人,是不一樣的。(翻攝自中視新聞)
改變結構從行動開始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處於半邊陲的台灣人,在抬頭仰望白皮膚的「優越他者」的同時,複製了殖民之眼的凝視,低頭蔑視膚色更深的「低劣他者」。[/epq-quote]以上簡要地介紹了社會學中有關種族主義的相關概念,並且分析了台灣社會的種族主義,如何呈現一個我稱為「階層化的他者化」的社會體制(註5)。你也許在想,這樣的社會學的分析,可以告訴我們如何改變社會嗎?
尤其是,當你說種族主義是如此龐大的結構體制,渺小的個人如何可能撼動?
結構性的問題確實沒有急就章的解決之道,但不要忘記社會學理論所提醒我們的:如果結構是一面高牆,其中的一塊塊磚頭是透過個人的日常行動所持續打造而成,換言之,我們的行動並非外在於結構,或單純受結構所制約,我們的行動參與了結構的再製,因而也蘊含改變結構的可能。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更反思地避免種族化刻版印象的再製,比方說,你在街上看到菲律賓人,不要馬上假定她是來台灣做幫傭;你在小吃店遇到越南人,不要劈頭就問她什麼時候嫁來台灣;你在火車站碰到外勞節慶擠滿了人,眉頭緊縮抱怨不方便時,設身處地想一想,他們不只是勞動力,也和你一樣,有對放假、休閒、社交的需求;你在海港邊碰到印尼船工,身體下意識地保持距離時,檢視你腦中浮現的形象是什麼?
想一想,他們也是別人的兄弟、父親、愛人。
當然,更重要的是結構層次的各項積極作為,舉例來說,我們的教育與文化政策對「國際化」、「多元文化」的追求,需要更多元的關注,而不是單純擁抱英語世界或歐美日先進國;除了空洞的法律宣示與官方說法,我們需要更有效地透過法律途徑以及社會教育來反對與制裁種群歧視與仇恨言論(註5)。
我 20 年前學德文的時候,在德國文化中心統一編定給全球學習者的課本裡讀到這樣的一課:一個南斯拉夫人,在德國打電話詢問租房子,一個房東問他,「你是德國人嗎?」當他回答不是,對方馬上掛電話。—— 德國有著種族仇恨的不光采過去,但他們面對的方式,不是粉飾太平,而是防止與教育。
面對不同樣態的種族主義,我們需要誠實自省、積極改變,而不是用擔心「破壞台灣形象」之名,拒絕照見我們的黑暗之心。
(本文原標題為〈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原作者為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原刊載於《巷仔口社會學》。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附註
- 2013 年 8 月,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批評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的出訪團隊,標榜原住民服飾,但配色或形式都不對,將原住民文化當做展演消費、錯誤呈現。
- 趙守博,1992,《勞工政策與勞工問題》,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頁145。
-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見李美賢,<別「菲律賓」了好嗎?─「再/遲到現代性」的焦慮與痛苦>,天下獨立評論,2013年5月19日。
- 我也要強調,西方移民在台灣也遭遇若干面向的歧視,其一,由於官方對於幼稚園外師的僱用限制,許多英文外師被迫用非法證件工作,可能發生被雇主箝制或剝削的情況。其二,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可以在台灣找到許多相關的工作機會,但他們也抱怨被窄化為「英語人」,難以擴展與英文無關的專業生涯,詳情請參見 Lan, Pei-Chia, 2011 “White Privileges, Language Capital, and Cultural Ghettoization: Western Skilled Migra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7(10): 1669-1693.
- 請參見藍佩嘉,2009,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第二章。
- 目前僅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反歧視條款:「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得依其受侵害情況,向主管機關申訴。」但法條如同虛設,參見鄭詩穎<台灣需有效的反歧視措施>,蘋果日報,2013年05月18日。
編按
- 不少讀者對於 Trayvon Martin 一案有不同看法,認為相關討論值得更細膩,例如 Zimmerman 本身一半血緣為祕魯─非洲血系,其種族認同是拉丁美洲裔(Hispanic),也不會被一般白人社會認為是白人。參見原文討論。
延伸閱讀
關於作者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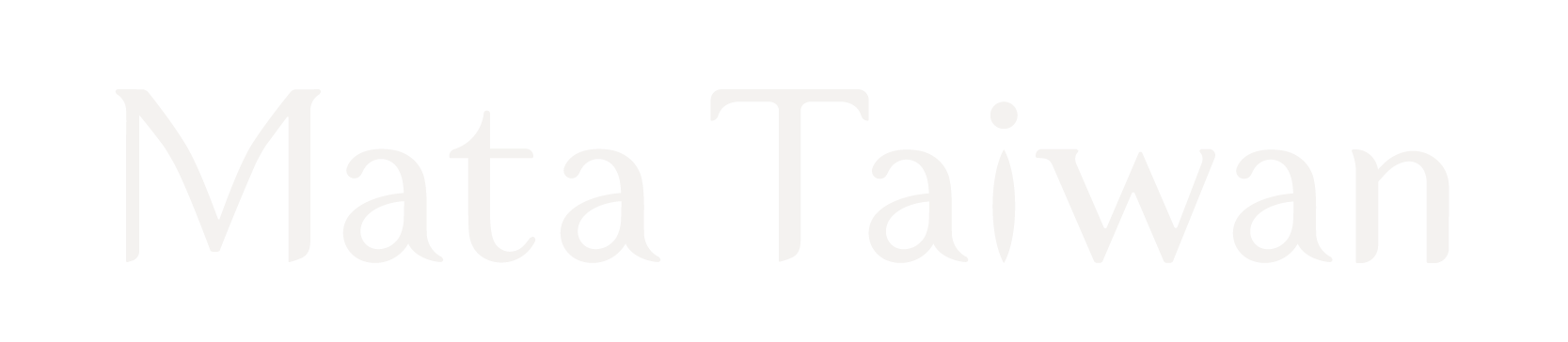




Leave a Reply